一桩无差别杀人事件,被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撕开了现代社会的伤口,致使我们不得不直面人性的复杂,还有法律的困境 。

悲剧的根源
电视剧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大结局是宋乔安和刘昭国终于坦然面对失去儿子的伤痛,美媚也决定要一直支持王赦,让王赦坚持做他想做的事情,而思悦和大芝也在相互扶持下努力的生活着。
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剧情简介:品味**台编辑主管宋乔安(贾静雯饰)的儿子是两年前李晓明(王可元饰)无差别杀人案件的罹难者,先生刘昭国(温升豪饰)是网络先驱报的创办人,夫妻在儿子走后因现实磨难渐行渐远准备离婚,但11岁的女儿天晴(于卉乔饰)行为却日渐失序,为了女儿终逼二人必须重新检视自己身上的伤口。李晓明的辩护律师王赦(吴慷仁饰),在李晓明死刑定谳之后,仍想要了解其犯罪动机,锲而不舍的他,开启了众人命运的连结。
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是由林君阳执导,吕莳媛编剧,贾静雯、吴慷仁、温升豪、周采诗、曾沛慈、陈妤、施名帅等主演的**写实剧。该剧讲述了在一起精神病患随机杀人事件之后,受害者家属、加害者家属、辩护律师及其家属、一般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属、公共媒体以及精神病院面对伤痕、重建生活的故事。该剧于2019年3月24日在**公共电视台首播。
该剧背向观众,抛出一个个问题,从而提供了思考世界真相的入口,也是深层关怀的起点。作为一部犯罪与人情题材的群像剧,各种身份的人连番登场,不断破解和挑战观众的“安全感”与常识。迎合观众口味的作品常常是“娱乐至死”的面孔,多少会背离艺术的自律性,但“轻松”本身也无可厚非,这些“未必可靠却乐观”的心理按摩与救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。制作方通过数据库剖析、总结热点,并成功的落地、结合文化本土化,使得剧集呈现了一种坚硬、真正切中现实的痛点。
李晓明于影院开枪,致使多条生命被夺,其行为被界定为无差别杀人,此罪行并无特定目标,凶手和受害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,这让悲剧更具随机性以及恐怖感,案件发生之后,社会陷入恐慌状态,人们开始对身边的陌生人是否隐匿着危险产生质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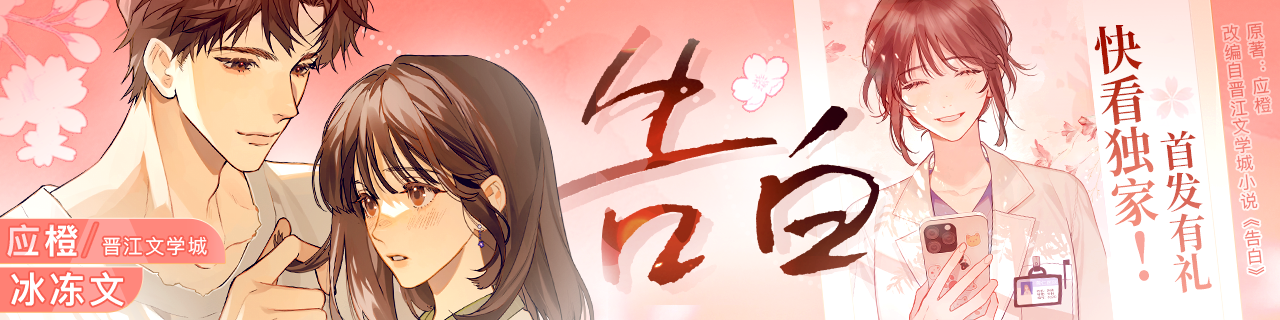
剧中未明确交代李晓明的犯罪动机,他本来是个有理想的普通人,经历多次失败后产生了反社会倾向,这种角色设定折射出当代社会竞争压力对个体的侵蚀,还引发了对心理健康的关注,他的家人因此背负了沉重枷锁,在愧疚与痛苦中挣扎求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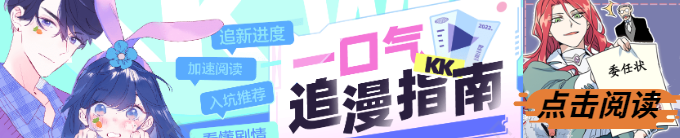
加害者家属的困境
在那事件发生之后,凶手的父母,凶手的妹妹,变成了众矢之的,不得不隐匿身份去生活,他们所经营的面店,被迫关上了门,家庭经济进入了困境,更为残酷的现象是,网络暴力,现实排斥,致使他们很难重新融入社会 。
李大芝身为妹妹,于媒体领域开展工作,然而却居然不敢去公开自身身份,这般双重生活实在是令人感到窒息。在剧中呈现出,身为加害者家属同样承受着持久创伤情况,他们既已然失去了亲人,同时又还要背负着社会谴责,如此双重惩罚进而引发了对于集体正义界限的思考。
受害者家庭的创伤
宋乔安身为新闻台编辑,在枪击案里失去了儿子,而后她陷入了酒精依赖的状态,也成了工作狂,她和丈夫的关系产生了裂痕,还对幸存的女儿疏于照顾,呈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典型症状 。
寻求慰藉所选择的另一受害者家庭,采用诉讼方式,然而在漫长司法程序里消耗精力。剧中多个家庭,呈现不同应对方式,有的家庭,被仇恨吞噬,有的家庭,尝试宽恕,揭示创伤修复的多元路径。
辩护律师的挣扎
被全网抨击的律师王赦,为死刑犯进行辩护之举,连家人都对他的这般选择深感不解,他秉持着一种理念,即了解犯罪动机才能够预防悲剧,即便处于舆论压力之下,依旧在各个案件之间来回奔走 。

在一场戏里,他遭到受害者家属泼粪予以侮辱,然而他依旧坚持法律程序正义,这个角色对法治社会里律师的职责以及道德困境作出诠释,还点明了“程序正义”对于保护每个人权利的重要意义 。
媒体的角色与责任

在剧中,新闻台为了追求收视率,过度地去渲染案件细节,这因而对受害者家属酿成了二次伤害,记者在争抢新闻之际,忽略了伦理底线,甚至于还把加害者家属的隐私予以公布,这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。
宋乔安身为,媒体主管处于两难境地,一方面要维持媒体的生存,另一方面要守住新闻的底线,剧中所呈现的新闻编辑室日常,反映出了现实当中媒体在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艰难平衡 。
修复与重生
身份被勇敢面对的李大芝最后,与受害者家属展开对话,这种直接交流虽充满痛苦,却是双方疗愈的起始,宋乔安也慢慢走出阴霾,对家庭关系重新审视 。
剧终时,多个角色在废墟里寻觅着希望,法律判决没能终结伤痛,然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成了新的起点,这种开放式的结局暗自表明社会创伤所需的修复时间更长 。

这部剧有没有使你思索过,在悲剧出现之际,我们每一个人与恶行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呢,欢迎于评论区去分享你的看法,要是认为文章有启迪,请点赞予以支持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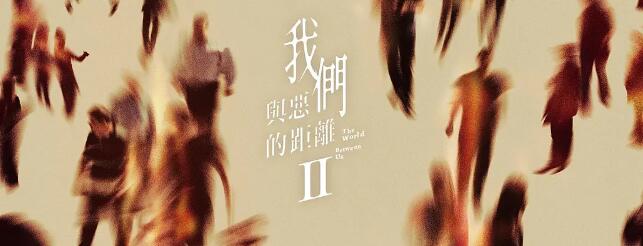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